緬懷學者趙老師
—紀念趙修竹教授百年誕辰—

趙修竹教授
(1920.07.23—2003.12.26)
趙修竹教授是我崇敬的前輩,我與其他同事和晚輩都習慣稱他為趙老師。
趙老師于2003年病逝,享年83歲。彼時應《中國免疫學雜志》之約,筆者曾撰文緬懷。該文是在專業刊物發表,主要介紹趙老師生平和學術成就,一定程度上屬“官樣文章”。多年來一直有個心願,想從晚輩、學生的角度撰文紀念趙老師。
2020年7月23日是趙老師百年誕辰,特撰此文回憶他生前工作和生活的若幹片段,以茲紀念這位令人敬仰的前輩學者。
同濟醫學院是百年老校,人才荟萃,許多道德、文章皆可為人楷模的前輩學者曾在同濟任教。
有人将科技人員分為兩類:大多數是科技工作者,他們多出于敬業和本分而完成本職工作(其中少部分則僅為稻粱謀);為數不多者屬科學家,他們全身心地探索學問,并非單純追逐名利,而是源于對學術的興趣和熱愛,以求揭示自然現象的本源。
毋庸置疑,趙老師屬後者,是同濟醫學院教師群體中名副其實的科學家。
*獻身學術、終生不渝
趙老師曾多次說過:“我這一生,沒有一天偷過懶”。這句話是他對自己終生所為的如實寫照。
由于曆史的誤會,未屆不惑之年的趙老師于1957年被錯劃為“右派”,此後20年間陷入人生的低谷。但即使身處逆境,面對政治上的歧視和生活上的窘困,趙老師探究科學真知的初心從未動搖。他在缺少經費、設備及助手的艱難情況下,不計毀譽,曾先後開展“中國人體的體液分配”、“高溫作業對人體的影響”、“抗腫瘤藥物篩選”、“腫瘤免疫”、“核磁共振”、“補體”等領域的科學研究,并取得諸多成果。
趙老師平生唯一的愛好是閱讀專業文獻,可謂手不釋卷。因此,他往往最先掌握醫學生物學領域的新技術、新觀點和新理論,被校内外同事和同道譽為“活字典”。據馮新為教授回憶,在上世紀60-70年代,他曾從趙老師處分享許多醫學領域的最新信息(如前列腺素、核磁共振等)。
趙老師知識淵博,對許多科學問題有自己獨到的見解。例如,他于1985年在一篇關于補體C4遺傳學進展的綜述文章中,首次提出基因locus應翻譯為“基因座位”(site才是位點)。這個意見日後獲得國内學術界認可。
趙老師這一代學者多具有深厚的人文底蘊,堪稱智者。他在闡述自然現象及其規律時,往往上升至哲學和倫理的高度。筆者作為晚輩,深感與趙老師交談如沐春風,受益匪淺。
在一次令人印象深刻的交談中,趙老師論及HLA複合體複雜的基因多态性(polymorphism)時,引用了黑格爾的名言“存在即合理”。趙老師并由基因多态性現象,引申至自然界及人類社會的多樣性(diversity)及其生物學意義:“源于自然選擇及進化,自然界的生物和生态具有極為豐富的多樣性,彼此互補并相互依存,從而構成了絢麗多彩、充滿生機的大千世界;人群中“表型(phenotype)”(外貌、品性)各異的芸芸衆生,更是多樣性的範例,他們的出生、經曆、價值觀、信仰、種族、民族等千差萬别,通過彼此不斷的碰撞、沖突、互讓和包容,從而組成了生氣勃勃并不斷進步的人類社會。”
改革開放之前,我國财力有限、外彙稀缺,也未受國際知識産權聯盟的制約。地處西安的一個“内部”機構專門負責翻印國外的重要學術期刊(其紙張、印刷、裝幀均十分粗糙,不堪恭維),供國内科研、教學機構訂閱。尤其是“十年動亂”期間,名目繁多的政治運動接踵而至,多數專業人員無心鑽研學問,圖書館門庭冷落。此時的趙老師,成為這些“盜版”期刊最忠實的讀者。據趙老師自述,當年他從未漏過任何一期《科學》和《自然》雜志。至今,若有心人去學院圖書館查閱上世紀60-70年代的學術期刊,還可發現有些文獻上存留有趙老師閱讀時留下的鉛筆記号。

同濟醫學院圖書館館藏的當年《自然》雜志合訂本
文革結束後,百廢待舉。面對專業人員知識老化、獲取科技信息渠道不暢的困境,由國家科委和衛生部批準,中國科學院醫學情報研究所于1978年組織國内各高等院校和研究機構分工創辦《國外醫學》(原名《國外醫學參考資料》)系列雜志,我校獲準出版《國外醫學分子生物學分冊》。


當時,學校指派梁之彥教授(生化)挂名,由趙老師具體負責,會同丁惟培(藥學)、馮宗忱(生化)、趙轶千(生理)等教授籌建編輯部。1980年底,聘請國内相關專業的知名學者組成編委會,梁之彥教授和趙老師分别任主編和第一副主編。是時梁教授已年逾八旬,趙老師實際上承擔了執行主編的重任。梁教授于1986年8月逝世,趙老師遂接任主編,直至2001年。20餘年間,每一期雜志從确定主題,到約稿、審稿、定稿,趙老師都親力親為。
在趙老師及其同事們的辛勤耕耘下,《國外醫學分子生物學分冊》很快成為廣受國内生物醫學專業人員歡迎的信息來源,訂戶超過7000。許多當年的年輕讀者或撰稿者,多年後陸續成長為各專業領域的領軍人物。不少人至今未忘,自己的學術生涯中曾獲益于這本有啟蒙意義的學術刊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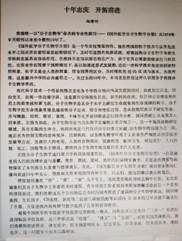
趙老師撰文“十年志慶 開拓前進”
*老骥伏枥、壯心不已
文革結束後,改革開放喚醒了中國人和中國科學家。已近花甲之年的趙老師也迎來了科學的“春天”。上世紀70年代末至90年代初,是趙老師煥發活力、學術生涯最精彩的一段時光。由于從未虛度年華,趙老師對國際上醫學生物學新進展有較深入的認識,并選擇位于HLA複合體的補體基因多态性及其與某些自身免疫病的關聯,作為研究方向。
當年,國内科研條件之簡陋,超乎一般人的想象。趙老師實驗室僅有的設備是水平離心機、台式高速離心機、蛋白電泳儀等。就在這樣的艱苦情況下,趙老師帶領課題組成員獲得一系列科研成果,發表多篇高水平論文。
我國于上世紀80年代初設立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彼時國家财力有限,面上項目的資助額度一般為2-3萬元(最低僅8000元)。此項基金成為當年國内廣大科技人員競相争取的重要經費來源。趙老師以自己紮實的前期研究成果為基礎,于1985年獲得首批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4萬元),開展“中國人補體C4的遺傳學研究”,以後又屢獲資助,成為同濟醫大教師隊伍中的佼佼者。
上世紀80年代,趙老師的研究進展受到同行專家矚目,多次在國内外學術會議上報告,先後榮獲多項國家教委、衛生部及省市科技進步獎。為推廣補體基因遺傳多态性研究的相關成果,趙老師課題組曾多次舉辦理論與技術學習班,促進了國内在該領域的研究工作。
趙老師在補體基因多态性領域的研究進展也受到國際學術界的關注。趙老師課題組成員張文傑于1986年赴西澳大利亞大學醫學院附屬皇家佩斯醫院臨床免疫科做訪問學者,該科主任Roger Dawkins(羅傑▪道金斯)教授的研究領域與趙老師相近。經張文傑牽線,1989年,Dawkins教授和趙老師聯合申請了澳大利亞教育部“澳中教育合作基金”,由同濟醫科大學與西澳大學在武漢共同建立了“中澳友誼補體實驗室”,澳方提供了6萬澳元,用于購買科研設備。其後,該室被第11屆國際組織相容性學術會議列為全球10個補體定型中心之一。

中澳友誼補體實驗室的澳方負責人Dawkings教授來訪(1990年)
在趙老師一生的學術生涯中,對補體遺傳多态性的研究工作占有重要地位,所發表的論文占論文總數的80%以上。因此,從上世紀70年代起,趙老師即萌發編撰一本《補體學》專著的念頭,以反映該領域最新進展。
當年,專業人員在國内正式出書絕非易事,首先必須獲得書号,後者是出版社待價而沽的稀缺資源。經多方聯系,湖北科技出版社同意出版此書,但首先必須支付3萬元購買書号(相當于當時趙老師約兩年的退休金),印數3000冊,作者自銷1000冊作為稿酬。因此,能否籌款3萬元成為決定出書成敗的關鍵。
免疫學教研室的同事們理解趙老師的這個心願,并用實際行動給予支持。當年教研室從事科技開發,略有積累,主要用于增添急需的科研設備。科室全體人員經過讨論,一緻同意出資1萬5千元資助趙老師出書,不足之數則分頭四處“化緣”。
此前,校内各行政部門從未有過資助教師個人出版專著的先例。但是,受趙老師百折不撓、終生做學問的精神所感召,同濟醫大基礎部、科研處、教務處、研究生處、校辦等單位都破例慷慨解囊,共同解決了這個大難題。
趙老師于90年代初退休後,耗費多年心血(其間還曾因罹患胃癌而入院手術),國内首部《補體學》專著終于在1998年元月問世。當出版社将樣書送交趙老師過目時,他的激動難以言表。事後趙老師曾撰文,談及拿到新書時的欣喜心情,并引用克雷洛夫(俄羅斯著名詩人)的詩歌來形容自己的感受:"在自家的蜂巢裡,看到了自己釀的一滴蜜"。

*學者風範、堪為師表
我于1980年調入同濟醫學院病理生理學教研室任教。當時正值改革開放之初,每周二下午是雷打不動的政治學習時間,不得無故缺席。我就是在一次例會上初識趙老師。至今還留有深刻印象,他衣着普通,不修邊幅,講話帶有濃重冀南口音,在例會上鮮少發言。以後接觸多了,才發現趙老師十分健談,并對晚輩和後學關愛有加。


趙老師和病理生理學教研室的同事們合影(分别攝于上世紀80年代初和80年代中)
上世紀80年代的中國高等教育,萬象更新,為開展素質教育并提高教學質量,校方大力推進教學改革。病理生理學教研室的知名教授趙修竹、馮新為、王迪浔等,當時都親自領銜組織課外科研小組,做了有意義的探索,在同濟醫大學生中廣有口碑,受到熱烈歡迎。
彼時,趙老師身邊聚集了10餘位學有餘力并熱愛科學研究的大學生。他們參加趙老師課題組的科學實驗,并定期舉行讀書會,不拘形式地讨論、交流國際核心期刊登載的最新科研進展。我有幸于1980年代末參加過一次趙老師組織的讀書會,當日的主題是胞内信号轉導。會場的氣氛極為熱烈,年輕人活躍的學術觀點及不懼權威的蓬勃朝氣,使我深受感染和鼓舞。
此項活動堅持多年,人員時有更替,但探索科學真知的宗旨始終未變。莘莘學子在趙老師指導下,不僅培養了科學思維和動手能力,部分學生還與趙老師共同發表綜述論文或參與撰寫學術專著,并獲湖北省優秀大學生科研成果獎。
趙老師是嚴師,對課題組成員和研究生要求十分嚴格,一旦發現有差錯,往往不留情面,嚴厲批評。但實際上,趙老師真心關懷屬下每一個人的成長和進步。他先後推薦課題組多位教師出國深造。這些人日後在國内外創業,均取得不俗的成就。凡有學生在國内外發表論文,趙老師都難掩心中的喜悅,并立即通過郵箱轉發給我。每當有遠道的學生來訪,趙老師的高興和激動,更是溢于言表。

趙老師與課題組部分成員合影(從左至右:翦必希、姜曉丹、趙老師、汪策、吳鋒)(1980年代末)

博士研究生吳雄文論文答辯會(1993年)

趙老師喜形于色,與課題組成員和研究生在新成立的中澳合作補體實驗室合影(1991年)

有學生自遠方來,不亦樂乎!在德國行醫的姚竹專程探望趙老師(2003年春)
我和趙老師原來同在病理生理學教研室任教,科研方向均為免疫病理。鑒于現代免疫學理論和實踐突飛猛進的發展,自1980年代初開始,國内多所重點醫科大學先後成立了免疫學教研室。
1988年我由德國進修返校後,病理生理學教研室的趙修竹、馮新為老師和原微生物學教研室的畢愛華老師分别與我約談,鼓勵并邀請我一起參與,在同濟醫科大學創建獨立的免疫學科。

首先倡議并參與創建同濟醫學院免疫學教研室的三位前輩學者(右起為趙修竹、馮新為、畢愛華)(1990年代初)
同濟醫科大學免疫學教研室于1989年成立後,三位前輩甘當人梯,推薦我負責牽頭,并對學科的發展和規劃提出許多寶貴建議,對我本人的工作更是始終不渝地給予充分尊重和大力支持。

趙老師和參加湖北省免疫學會年會的免疫學系師生合影(第二排右起盧昌秀、畢愛華、郝連傑、武忠弼、馮新為、趙修竹)(2001年)

趙老師和免疫學系教師宴請回國來訪的老同事(2000年)
趙老師90年代初任中國免疫學會常務理事及湖北省免疫學會理事長。筆者回國不久,趙老師即力薦我接任省學會理事長。1993年在南京召開中國免疫學會第二屆理事會,趙老師又推薦我接任常務理事。由于此前我主要參加病理生理學專業的學術活動,與免疫學界同道接觸甚少。為此,趙老師在會議期間逐一約見多位免疫學界前輩,親自登門懇請他們給予支持。
全國科協屬下的各專業一級學會有數十家,是開展學術交流的民間團體。專業人員在學會兼職,一定程度上反映其所在單位和學科的學術水平。趙老師高風亮節,為扶植成立不久的同濟醫大免疫學教研室,付出艱辛的努力。此後時隔多年,多位免疫學界前輩還屢屢向我提及,像趙老師這樣全心全意為後學的晚輩盡心、盡力,實屬不易和罕見。往事曆曆,我至今銘記在心(并非單純因為筆者是趙老師的接任者)。
有個插曲值得一提。趙老師關愛後學晚輩,年輕人也敬重這位令人仰慕的前輩學者。按照與出版社簽訂的協議,作者須負責自銷1000冊《補體學》。為此,專著正式發行後的數年間,凡是參加國内舉行的學術活動,免疫學系的年輕教師和研究生均不辭辛苦,主動帶若幹冊《補體學》與會,設攤賣書,成為會場中一道引人注目的獨特“風景線”。
趙老師為人耿直,易激動,無意之中,所言所行難免得罪人。但是,趙老師的“火氣”都是因為公事而引發,從未因私事與他人結怨。我在校内路遇相識的職能部門工作人員,對方有時會“告狀”:“你們的趙老師又來我們辦公室發脾氣了。”雖然如此,他們了解趙老師的性格和為人,在政策允許的範圍内,都盡可能給予關照和支持。
趙老師這一代讀書人,深受中國傳統文化熏陶,人際交往講究禮數周全。先母于2002年病逝,彼時趙老師已永久性置入導尿管,不良于行。聞訊後,趙老師來電話召我去他府上,除表示慰問外,堅持要奉送奠儀。經我再三解釋,先母遺願喪事從簡,謝絕一切饋贈,趙老師才作罷。
馮新為教授與趙老師于50年代初一起創建武漢醫學院病理生理學教研室,80年代末又共同倡議和籌建同濟醫科大學免疫學教研室,兩人相識、相知逾40年。1993年年初馮教授70大壽,趙老師親自登門祝賀。

*春蠶到死絲未盡
趙老師一生從教,專業和學問占據了他生命和生活的全部,此外别無其他愛好。至1998年《補體學》專著正式出版,趙老師曆時半個世紀的學術生涯劃下了句号。
長期以來,疾病一直給趙老師造成很大的困擾。上世紀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趙老師曾患肝硬化、腹水,幾近昏迷,經搶救才轉危為安。至1990年代中期,他又先後罹患胃癌和尿道梗阻。晚年的趙老師飽受多種慢性病折磨,身心疲憊,且随年齡增長,健康狀态每況愈下。此外,趙師母罹患頑疾,時刻需人陪伴和照顧,也成為趙老師晚年揮之不去的牽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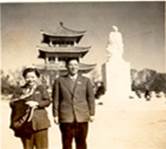
趙老師伉俪(1960年代攝于武漢東湖)

趙老師與趙師母最後的合影(2003年春)
趙老師的宿舍樓緊鄰我的住處。下班回家,我不時順道去探望垂暮的老人。趙老師家在一樓,卧室兼書房的窗戶面對門前的小路。常見的場景是,趙老師枯坐在書桌前沉思,目光中流露出萬般孤獨和寂寞,以及難以排解的空落。
趙老師曾多次向我談及自己曲折的一生:年少家貧;在抗日戰争動蕩的歲月中完成中學和大學學業;解放初期曾相對平靜地從事教學和科研;57年錯劃為右派後的20年間,受到不公正的對待(尤其是在文革中曾被誣告,無端遭嚴厲批鬥,一度有輕生之念);改革開放後不忘初心、重振旗鼓,但也不免懷有壯志未酬的遺憾。

趙老師舊居門前,左邊窗戶的房間即是他的卧室兼書房
雖然曆史及人生不存在“假如”和“如果”,但回顧趙老師的一生,筆者在緬懷之餘,有時仍然不由遐想:“當下中國的國力及科研投入,與30多年前相比已不可同日而語。晚輩學者如今的境況、機遇和發展前景,老一代學者難以想象和企求。憑趙老師及其他諸多前輩學者的敬業、勤奮和才智,他們若能生活和工作在今天,将會取得何等成就!”
筆者就記憶所及,拉拉雜雜地追述往事,言不盡義。謹以此文緬懷逝者,并紀念學者趙老師百年誕辰。
同濟醫學院免疫學系
退休教師龔非力
2020.07于武漢
本文撰寫過程中,得到趙老師生前同事、課題組成員及學生的熱情支持,提供了許多珍貴的史實和照片。他們是:馮新為教授、吳雄文教授、姜曉丹老師、鄭芳教授(免疫學系)、王迪浔教授(病理生理學系)、王維焱老師(學報編輯部)、鄒立君教授(同濟醫學院圖書館)、張文傑教授(新疆石河子大學)、汪策醫生(美國芝加哥)、姚竹醫生(德國慕尼黑)。在此一并緻謝,并共同緬懷趙老師。
趙修竹教授簡曆
1920.7.23
出生于河北省武安縣
1946年
畢業于原國防大學醫學院(第二軍醫大學前身)
1946~1949年
原國防大學醫學院生理學系任助教
1949~1950年
湖北省武昌醫院内科醫生
1950~1952年
武漢大學醫學院生理學系助教、講師
1952~1955年
中南同濟醫學院生理學系助教、講師
1955~1956年
在北京參加全國病理生理進修班學習
1956~1989年
創建武漢醫學院病理生理學教研室(現同濟醫學院病理生理系前身),任教研室主任,1956年晉升為副教授,1982年晉升為教授
1989~1993年
同濟醫科大學免疫學教研室教授
2003.12.26
病逝
趙教授長期承擔生理學、病理生理學、免疫學課程學工作;多次參與全國規劃教材編寫;曾從事高溫作業工人循環系統研究、變态反應研究、抗癌藥物篩選、卵巢癌腫瘤抗原研究等多項課題的研究工作,發表論文十餘篇
1970年代後期開始,趙教授在國内首次開展中國人群HLA-Ⅲ類基因遺傳多态性研究,在國内外學術刊物發表論文100餘篇,科研成果多次獲國家教委、衛生部、湖北省獎勵;
趙教授曾任同濟醫科大學中澳友誼補體實驗室主任、《國外醫學(分子生物學分冊)》主編、《中國病理生理雜志》及《中國免疫學雜志》副主編,并主編《補體學》、《病理生理學》等專著10餘部。
趙教授是湖北省/武漢市免疫學會和病理生理學會的創始人,曾任中國免疫學會常務理事、湖北省免疫學會理事長、中國病理生理學會常務理事、湖北省病理生理學會理事長、中南六省生命科學前沿論壇主席。
2022年5月
 學院官方微信
學院官方微信